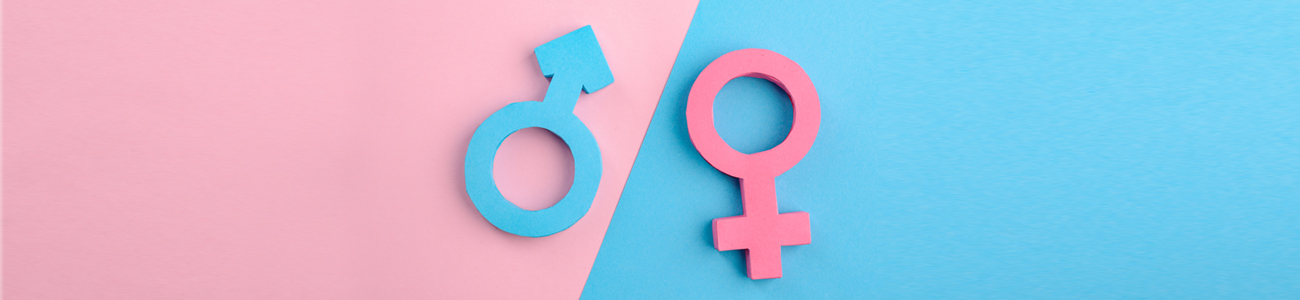唱歌那件小事與「性別展演」
文 /陳喬
作為生理男性,我的性別認同歷史中有兩條時間軸:
一條代表外於身體的,感覺的種種經驗疊加積累,軸線上的箭頭朝著社會化、「正常人」的方向指去。
另一條則潛在於身體,不可言說,是心靈與意識內容的加總,箭頭指向一個我真正的,或者想成為的模樣,無所謂正不正常。
兩條時間軸在認同歷史上,在我的身體經驗中,從聚合到慢慢地脫離彼此,平行,又不斷地嘗試縮短兩者的距離。
舉唱歌這個例子說明或許會更清晰。
在還未進入青春期,尚未變聲的九、十歲年紀,我總愛唱歌,唱女聲原音調的歌。
我還記得去庭園式KTV和大我五歲的姊姊對唱〈珊瑚海〉,總是我唱女聲、她唱男聲。隨後,青春期的到來如一把利刃,一刀兩斷地把這份美好切割開來,一半停留在姊姊身上,多年以後她的聲音依舊;另一半,即我男女莫辦的童音,則永遠駐留在過去了。
當然,渾然不覺的性別概念也隨即混入我青春期的性徵中,「生理性別」與「社會性別」愈來愈像雙色的棒棒糖,千萬條細長的糖絲緩慢地被黏在一起,從此密不可分。
青春期前我總唱S.H.E.或張惠妹的歌,沒有人有意見。
變聲後聲線逐漸低啞,歌聲總像蓋上蓋子一樣悶悶的唱不響亮,在KTV點女歌手的歌也逐漸被視作不正常,家人、親戚、朋友都問:「為甚麼不點一些周杰倫、羅志祥的歌?」我說音太高唱不上去,他們能接受;我說不喜歡,他們就納悶了。男生怎麼都盡唱嗲聲嗲氣的歌?為什麼不聽男歌手的歌?我猜想他們心裡充斥著這些問題,只是基於很多原因不問出口。
.JPG)
圖源/pixabay
回到認同史的角度看,變聲這個性徵似乎象徵兩條時間軸的初次分別,青春期捉走童音,卻沒有連著我喜歡的、想擁有的歌聲一起帶去。
隨著性徵愈來愈突出,那顆應該視作男子成熟象徵的喉結,對我而言卻是噎在喉頭的一顆毒果實。可是與此同時,不把它吞下去才是「正常」的,如同社會化過程聽見其他人說的「男生不能愛哭」、「男生要有擔當,有肩膀」等話語,沉重,卻仍要聽從。
在大學以前,我從一個拿起麥克風那麼自信的小毛頭,長成一個喉結明顯的少年,年過一年拿起麥克風的姿態卻愈加退縮。
有幾次亟欲得知自己歌聲是甚麼樣子,錄下自己的歌聲,放音時一個全然別於我的想像的低啞歌聲從手機跑了出來,如同一隻怪物站在面前。我害怕地不敢面對,選擇忽略,那之後再也不敢主動和其他人去KTV。
我明顯地感受到兩個時間軸分離、甚至疏遠的關係,卻也承襲青春期以來的社會性別概念,以至於羞愧感隨時間愈加明顯;對外保留地稱自己不愛唱歌,對內卻覺得自己唱歌難以入耳,害怕歌聲裡那隻怪物再次出現。
大學時重拾唱歌的自信,最大的契機是蘇打綠的主唱青峰和張懸。兩個歌手巧合似地顛覆青春期後我對男女歌聲的認知,前者音調高而輕柔;後者音調低而沉穩,我在兩個倒過來的極端中重塑自己的歌聲,過程中不停反思聲音、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關聯。
那一陣子發現自己唱張懸的歌總用男性化的口吻,唱蘇打綠的歌聲音則會偏陰柔。
或許是這一點讓我逐漸體驗到如同茱蒂絲‧巴特勒(Judith Butler, 1956-)所說的「性別展演」概念。
這個概念簡單地說,就是
性別可以被行動演繹,能像穿衣一般自由地去選。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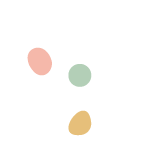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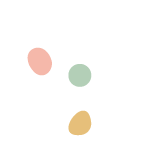
唱歌的特定口吻與聲音表現,對我而言就像在展演性別。兩位歌手又讓我意識到,生理性別並不侷限展演。
而長期以來把生理性別當作行為依據的我,在自我內部製造出了矛盾,亦即:明明想唱出陰柔的女聲,生理男性的身分卻使我不能選擇這種屬於女生的行為。
這個發現使得兩條徬徨不定的時間軸終於重新彼此牽引──關乎正常與否的社會化軸線與追求自我的軸線之間,經歷了從青春期起的矛盾與平行的長期狀態,又一次地開始聚合了。